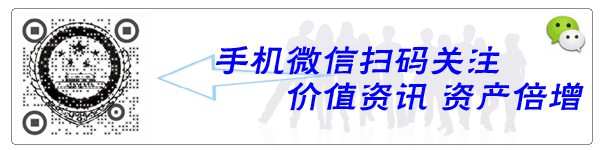2019-8-25 10:57
来源: tansuoyuzhengming
编者按
“垃圾”是我们每个人生活中难以回避的部分。近些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特别是电商经济和共享经济所带动的快递、外卖等上门服务、智慧生活的铺开,“垃圾围城”现象几乎成为中国大大小小城市的“痛点”。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便开始生活垃圾分类试点,遗憾的是历次垃圾分类皆收效不佳。今年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出台,“垃圾”议题也随之再次置入民众的视野。本刊尤为关注三点:一是此次上海生活垃圾分类中显现的最棘手的问题和应对之策;二是垃圾围城、垃圾转移现象背后所折射的城市经济发展模式的顽疾;三是从当下的垃圾战争看中国发展循环经济和城市文明的新契机。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教授。
中国城市正面临一场没有退路的“垃圾战争”
——诸大建教授访谈录
诸大建 |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
李梅 | 《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主任
本文将刊于《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9期
当前上海生活垃圾处理中的突出问题

李
诸教授您好!随着上海强制生活垃圾分类时代的开启,注意到您将其称之为一场“垃圾战争”的开启。您如此界定寓意为何?
上海生活垃圾分类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先行示范意义,可以从中讨论一些普遍性的问题。年初上海生活垃圾分类开始立法的时候,我曾称其为“垃圾革命”。革命一词当然具有更多的褒义,寓意着这是一个全新的起点。需要强调的是,垃圾革命不仅是要处理垃圾,即把城市产生的垃圾用环保且有效的方式分门别类处理掉;更是要减少垃圾,即避免和减少生产和消费中的垃圾产生。也因此,我现在更愿意称其为“垃圾战争”,寓意着这是一个分阶段、有难度的持久战,不会马到成功;同时,相对于以往的试点行动,现在应当进入全民动员、全民皆兵的状态。


诸大建
李
此次上海生活垃圾分类如果像您形容的是在打一场硬仗,那么您认为对于战争的认识需要达到怎样的高度,在战争的理解上是否存在一些“拦路虎”?
垃圾战争首先是思想的战争和思想的革命。我觉得,认识上的拦路虎主要是有两个:一个是上上下下对于这场垃圾战争的意义还没有深刻的认识,比如垃圾分类等于垃圾源头减量吗?垃圾战争是否包括不同阶段的目标?二是民众对自己在垃圾战争中的身份定位,以及对自己在生活垃圾分类中应尽的法律义务还没有深刻的认识。
对于第一个问题,垃圾分类等于减少垃圾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分类是把原先混合起来的垃圾分门别类,但垃圾总量并没有减少。说得精细些,我们需要进一步区别两个减量概念:一个是末端处理减量的概念,垃圾末端处理即焚烧和填埋的减量率等于厨余垃圾加上可回收物的量除以垃圾清运量;另一个是垃圾源头减量的概念,垃圾源头的减少率意味着城市垃圾的零增长和负增长。垃圾分类有利于减少末端处理量,但是不会减少垃圾的源头产生量。
如果说末端处理减量和垃圾源头减量还属于初阶目标,那么我们今天发起的这场垃圾战争的高阶目标,就是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变革,其直接起因是垃圾已经成为自水污染、空气污染之后的重大环境挑战。换言之,环境保护是垃圾分类运动的出发点和初心,是要在蓝天碧水的保卫战争之后,打一场规模更大、变革更大的城市环保战争。
实际上,垃圾分类处理的成本要比混合处理高出很多,但是混合处理下的填埋或焚烧会给城市带来很大的环境影响,垃圾分类就是要降低环境的影响,特别是通过把其中的湿垃圾分出来,大幅度提高焚烧的质量,减少填埋的比重。这是垃圾分类最主要的理由。人们喜欢说“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而我要说“垃圾没有分类就是污染而不是资源”。资源回收是可以志愿的,可以赚钱的;而污染治理是不可以志愿的,是需要支付成本的。
对于第二个问题,民众应该无条件地参与垃圾分类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是刚性的。在环境问题上,全世界的通行原则就是“谁污染谁负责”,对自己造成的垃圾污染负责,这是每个人都应尽的法律义务,而不存在愿不愿意进行垃圾分类的问题。可以说,垃圾战争就是中国城市的一场没有退路的强制性参与的人民战争。我认为,在水、气、土、渣等城市环境问题中,垃圾处理是城市最大的挑战。对此,不能等待每个人的觉悟提升,有时候必须采取疾风骤雨式的集中治理,然后转化为全社会成员的长期坚持与习惯养成,两相结合,这样才能取得实效、巩固成果。


诸大建
李
的确,对于民众来说,只有明确了“我是一个兵”,“我为什么而战”这种本源意义上的问题,才真正有利于“垃圾战争”的稳步推进。而以什么样的战略或者说治理模式推进垃圾战争,如何让“士兵”们的行动跟上节奏,从外部强制到内部主动,则是接下来要追问的。
就治理模式而言,我认为上海的垃圾战争体现的是一种高层发动、政府合作、社会参与的城市合作治理模式。它既显著区别于1970年代日本东京自下而上的邻避博弈,最初发起于江东区对垃圾填埋的邻避反抗,然后成为东京都23区的社会自治;也区别于2000年以来,上海由狭窄的主管部门推进、简单的自上而下宣传和民众志愿参加结合的行动。
它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主要领导人的直接动员,呼吁垃圾分类是新时尚,上海还为此召开了多年没有的万人动员大会,使得垃圾分类上升为城市发展与治理的战略性事件。二是超越了以往垃圾分类局限于市容环卫局的情况,强调政府条与条、块与块、条与块之间的无缝隙整合,这突出表现在垃圾分类管理贯穿于四种垃圾的投放、收集、运输、处理全过程,是以往的垃圾分类没有做到的。当然,万一连条块之间都不顺畅,我们还有党建的空间。三是制定法规和加强教育,强调垃圾分类是污染治理,需要强制推进,全员无条件参与,同时鼓励大家因地制宜解决问题的创造性。正是基于以上三点,这次垃圾分类运动才可能一举突破以往十几年的缓慢发展,进入到疾风骤雨式的革命化进程。这样的动员模式在欧美城市治理中是不多见也不可能的事情。


诸大建
李
那么,就这场战争的战术或者说具体操作的方式、方法而言,您觉得此次生活垃圾分类中存在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上海的生活垃圾现在实行四分类,即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这种分类与上海作为沿海城市的垃圾特征相适应。我国城市人多地少,而餐饮垃圾中水分居多,因此对垃圾的末端处理方式应该从填埋为主转化为焚烧为主。垃圾分类分出干与湿,就是为了便于焚烧。其中,湿垃圾或者说厨余垃圾又是垃圾处理中最主要的挑战,也是最有争议性的焦点问题。
厨余垃圾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投放厨余垃圾时如何区分且分得有纯度,许多业内人士认为把厨余垃圾分出来的做法是自找麻烦,因为厨余垃圾区分一定要纯,而老百姓一般做不到这点。二是处置后的厨余垃圾出路,以及如何更具经济性。的确,一天几千吨的湿垃圾,如果都用作堆肥是有困难的。上海曾经研究过用家庭生物粉碎机处理厨余垃圾直接排入下水道的方法,认为如果用得起的家庭有10%,每天可以减少垃圾1300吨。但问题是,粉碎机无法处理鱼骨头等硬一些的垃圾,下水道也有可能被堵塞,垃圾进入雨水管就更麻烦。也有人建议不以家庭而以社区为单位处理湿垃圾,这在郊区的社区也许可行,但在空间稀缺的城市社区中就有困难。
区分干垃圾和湿垃圾很大程度还是具有中国城市特色的事情。例如,被视为垃圾处理榜样的东京就没有采用这样的分类,东京是按可燃不可燃进行垃圾分类,厨余垃圾作为可燃垃圾焚烧处理。我国台北是少数几个把厨余垃圾分出来的城市,2000年左右台北开始推进垃圾分类,厨余垃圾则进一步分为当饲料的猪垃圾和当肥料的肥垃圾。不过,最近有信息说台北厨余垃圾最后也是焚烧的。当然,分出湿垃圾专门进行处理不仅具有挑战性,而且具有创新性。东京都厨余垃圾在可燃垃圾中占35%,虽然没有专门分类,但是据说近年来也有政府鼓励把厨余垃圾拿出来用作堆肥的做法,一方面产生资源化的效益,另一方面减少焚烧的压力和成本,关键是“求精不求多”。


诸大建
李
在您看来,怎样的厨余垃圾处理方式更加契合我国国情?
我认为,对待厨余垃圾要拿捏一个“度”,既要分出,又不要太分出。要分出,是因为厨余垃圾混在干垃圾里进行填埋处置、生化处置会影响焚烧处置的质量;不要太分出,是因为把厨余垃圾分得太精细,是成本高、收益小的事情。中国厨余垃圾占比约为60%,只要把其中20%生物质纯度高的垃圾分出来堆肥就很好了。对上海而言,在每天3万吨的垃圾中能分出25%的湿垃圾即7000吨左右,进行有质量、有出路的生物处理,已经非常好了。
我国城市的垃圾减量,最重要的是厨余减量,而厨余垃圾的减量有两个方面:一是扔垃圾的源头。比如,扔垃圾时要把厨余垃圾的水分沥干了,像一些城市社区就发明了中国式的厨余粉碎机进行处理,在郊区社区里就地堆肥不进入市政垃圾流等。二是生产消费的源头。比如可考虑采用可持续发展的nexus办法,把厨余垃圾与饮食、健康三者关联起来:从胡吃海喝到食物减量,减少浪费;从毛菜上市模式走向净菜上市模式,降低扔弃的厨余量;从做饭模式到外卖模式的消费模式变迁中,一定要控制相应的食物和包装垃圾。
总而言之,厨余问题的解决方案要有渐进式的战略思考,在当前我国干湿分类能力弱、处理成本高的情况下,可考虑只分出相对纯的生物质厨余垃圾,大部分厨余垃圾仍然通过焚烧解决;随着我国分类能力的提高和处理成本的降低,再逐渐降低焚烧比重、增加堆肥比重。


诸大建
李
此次上海垃圾分类中民众最大的吐槽点在于,“干湿垃圾不好分”以及“扔垃圾定点定时不便利”,您如何看待垃圾治理与民众感受之间的关系?或者说这场“垃圾战争”如何打得更加灵活和更富温情?
上海的垃圾从混合处理到分类处理,马路和社区要减少垃圾桶,标志着城市发展从增量扩张到存量优化的转化,反映了环境服从发展到环境倒逼发展的转型。垃圾分类的总趋势就是要从以前的太方便到现在的不方便,从以前的不用分类到现在的要分类,甚至从以前的免费到未来可能的收费。
尽管垃圾分类不方便,但是垃圾分类的思路应该尽可能“简洁”:干垃圾是焚烧处理的垃圾,就可以分得相对粗线条一些,其他垃圾的分类则应尽量精准。沿着这样的思路,简化版的垃圾分类操作方法可以是:先假定是干垃圾,然后依次做简单的排除法;再问是否会腐烂,如果是,就是生物处理的湿垃圾;进一步问可不可以卖点小钱,如果是,就是玻、塑、纸、金、布等资源垃圾。这样操作下来基本可以做到八九不离十。而对于不同的社区,上海其实也在鼓励不同的具体“战术”的探索。像垃圾定时定点的做法并不是一刀切,也只是约定而不是规定,给民众以温度感和人情味,从说服教育到强制性再到习惯的养成,逐渐达成更多的社区乃至社会共识。
垃圾处理本身还有上中下游几个环节:上游的投放,中游的收集、运转,下游的处置。此次上海颁布的条例针对的是所有环节,不仅前端要分类,后端也是一样,共同构成一个系统工程。为此,我们一定要做好持久战的打算。中国城市至少需要3~5年才可能把垃圾分类的环节完全做到位,而人们垃圾分类的习惯则需要十几二十年才可能养成。


诸大建
世界级的垃圾围城与垃圾转移的逻辑

李
当下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都有“垃圾围城”的现象,这意味着垃圾在和城市争夺“空间”,这也是一个世界级的现象。您如何理解城市的“垃圾空间”?
谈垃圾其实是在谈城市。就像人有新陈代谢一样,城市也有新陈代谢,垃圾围城的城市发展,就意味着物质代谢不良。长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发展,的确是以垃圾的大量产生、容易扔弃为代价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是党的一次“自我革命”,那么此次上海的垃圾新政也可以说是我们对城市垃圾问题的一次“自我宣战”。不仅如此,到2020年年底,我国将有46个城市实施垃圾分类政策,进行一场城市发展的全方位的自我革命。而垃圾分类问题的要害在于,城市发展一定要为垃圾产生和处理留出足够的空间;城市垃圾空间如果不足,我们的城市发展就会陷入非常被动的境地。
城市的“垃圾空间”是一个带有畅想意义的概念,我个人认为这个概念对于城市发展非常重要。对于垃圾空间,我们过去只是被动应对,现在从垃圾分类到垃圾空间,就是要求更加主动、更加绿色地做好城市空间的规划和管理。垃圾空间不仅包含末端的处理功能,也包含投放、收集、运输等功能。比如,上海老港垃圾场每天处理垃圾2万吨,占用土地约30平方公里,比例大约是1:1.5,即处理1000吨垃圾需要垃圾空间1.5平方公里,这里还不包括垃圾从投放到收集、转运所需要的空间。如果我们把这一比例放大到1:2,那么系统地处理1000吨垃圾就需要在城市发展中预留2平方公里的垃圾空间。
按照中国城市建设用地标准,如果每百万城市人口需要100平方公里建设用地,每人每天产生垃圾1kg即总共1000吨,那么需要预留2平方公里的城市垃圾空间用于生活垃圾的投放、收集、装运、处置等。按照这一标准,我们可以对上海垃圾空间的规划管理进行粗略估测。如果到2035年上海城市的服务人口峰值为3000万,而上海的人均垃圾日产量1.5千克基本趋于稳定,那么每天垃圾清运量大约为4.5万吨,城市垃圾空间安排至少不能低于90平方公里。如果城市的垃圾场多为单一功能,而不是像上海老港垃圾场包含了焚烧、堆肥、填埋等多种功能,那么城市还需要为垃圾释放更多的空间。


诸大建
李
我们生活在一个垃圾泛滥的世界,如果垃圾不从源头减量,一定会不断蚕食城市空间。而当城市自身无法消化这些垃圾时,就会出现城市与乡村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空间转移。您认为“垃圾转移”现象是否注定不可避免?
当今世界垃圾问题的解决方案其实主要还是空间转移的逻辑,而不是减少垃圾的循环经济的逻辑。比如说,我国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早些年的垃圾,就是简单运送到农村去堆放处理的。只不过随着农村生活的改善,农村人也开始反对外来垃圾,才不得不改变做法。
一般来说,垃圾空间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表现为,城市生产越发展、消费水平越提高,需要的垃圾空间就越多。在中国城市人多地少的情况下,垃圾空间的安排一定要有,但是不能无限制地扩张。我们可以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物质流的上下游关系,采取不同的政策举措:其一,在物质流下游的垃圾空间不够、上游的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阶段,政策重点应放在扩展和建设城市垃圾空间上,重点解决垃圾处理问题,包括处理不同类型垃圾需要的用地,以及投放、收集、中转、处理各环节需要的用地,我们可称其为“城市垃圾空间的增长型发展阶段”。
其二,当物质流下游的垃圾空间达到了规模和结构要求,就必须用下游稳定的城市垃圾空间来倒逼上游的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政策重点应放在减少和避免城市垃圾的过度增长上,可称其为“城市垃圾空间的质量型发展阶段”。


诸大建
李
当城市发展迈入您所说的“垃圾空间的质量型发展阶段”,特别是随着我国垃圾分类实践的深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垃圾空间的冲突是否也更易显现?
垃圾是城市的新陈代谢之物,垃圾空间现在愈发成为城市发展中卡脖子的问题。比如,一方面垃圾分类需要建设分门别类的处理设施,另一方面为这样的处理设施找到落地处却极其困难,会遭到或明或暗的邻避意识的抵制。又比如,一方面资源垃圾回收利用需要就地发展再生资源产业,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其实不太愿意拿出用地给这些经济收益小且有环境影响的企业。再比如,一方面,开发商造房的时候没有规划建设垃圾的堆放点,另一方面小区建成后物业把边门改造成了垃圾堆放点……到处都在上演垃圾空间的争夺战。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的城市对此并没有前瞻性的考虑,往往是遇到垃圾难题才被动应对,又常常因为邻避运动而屡屡碰壁。我们需要有足够的事先谋划,做好充分的战略准备。


诸大建
李
前不久,菲律宾与加拿大之间因“垃圾”爆发“外交战”,最终结果是满满69个集装箱被运回加拿大的温哥华。放眼全球,“垃圾转移”早已走出城与乡、城与城,走向国与国、区域与区域。您如何看待世界级的垃圾转移及其所引发的邻避运动?
我国对待垃圾转移的立场和态度近年来是有重大反转的。以废塑料为例,中国多年来是全球最大的废塑料进口国。2013—2017年间,我国大陆废塑料进口总额达232.26亿美元;排在第二位的是我国香港地区,进口总额为49.57亿美元;美国、荷兰、德国进口总额依次为12.63亿美元、11.61亿美元、9.66亿美元。2017年年中,我国环保部向WTO提交文件,要求紧急调整进口固体废物清单,于同年年底前禁止进口4类24种固体废物,开始彰显我国排斥洋垃圾的姿态,也终结了我国成为“世界垃圾桶”的历史。在此背景下,西方垃圾输出国开始把本国大体量的垃圾贴上“固体废料”的标签,出口至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沙特阿拉伯、印度等发展中国家。
“邻避”一词英文全称为“Not In My Back Yard”,翻译过来就是“不要建在我家后院”。世界性的邻避运动,其隐含的基本理论是,“垃圾尤其是会产生环境影响的垃圾,不可以随便空间转移”。这里的“不能随便”又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不能没有合法程序,二是不能不经过双方同意。垃圾的空间转移是任何人任何地方都感到讨厌的,无论是一个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转移,还是穷国和富国之间的转移。从“污染者负责”的角度看,各国也理应处置好自己产生的废弃物,不能向邻国转移污染物,推卸治理责任。而当发展中国家开始集体拒绝洋垃圾,就有可能倒逼发达国家实现“垃圾的就地化解决”。
对于日本这样的人多地少国家,人们印象中它的垃圾分类和回收利用做得很好。但其实它的垃圾处理方式也主要是焚烧,日本塑料、纸张等固体废弃物的本国回收率不足50%;日本废塑料2017年的出口量是143万吨,其中有52%销往中国。对于人少地多的国家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它们的垃圾处理方式以填埋为主、焚烧为辅,甚至找块空地就直接埋起来。纽约市的垃圾一般就是运到新泽西州或更远的州直接埋掉。在中国抵制洋垃圾的带动下,随着全球垃圾“禁废令”在联合国层面得到关注,未来几年发展中国家反对洋垃圾的运动估计会更加激烈。从另外一个角度,我想这也可以倒逼发达国家发动一场真正的垃圾战争,而不是用垃圾回收利用的名义做全球垃圾转移的表面文章。


诸大建
我国发展循环经济和城市文明的新契机

李
看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垃圾的空间转移只是缓兵之策、权宜之计,从人类共同体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而言,关键还是要转换到您所说的减少垃圾的循环经济思路上,不知主要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可否有可供借鉴的经验?
整体上看,发达国家的垃圾处理系统确实比发展中国家先进,其中德国是世界上“垃圾就地化解决”或者说把循环经济做得最好的国家。德国1996年便对垃圾回收利用进行立法,我国循环经济的最初思想就源自德国的“3R”理论——Reduce (减量化)、Reuse(再使用)、Recycle(回收利用)。在德国的循环经济模式中,有两点最值得我们学习:
一是把废弃物“资源化”(即Recycle)。最初世界上垃圾处理主要靠填埋、焚烧、堆肥三种方法。最古老的方法是填埋,其次是焚烧,再次是生物处理,如沼气发电、堆肥。但德国人认为这三种方法都没有在根本上重复利用垃圾中的资源,他们在思考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去做垃圾回收利用。比如,他们针对玻璃、金属、纸张、布料、塑料这些可回收利用资源,先做分类、回收利用,再做成原生材料投入到生产线中去。
二是生产能反复使用的耐用品,减少废弃物产生(即Reuse)。德国人认为,如果只忙着把垃圾处理掉,后边再怎么处理,也跟不上垃圾生产的速度,倒不如试着把垃圾减少。“reuse”与“recycle”的根本区别就是:它不是把垃圾破碎成物理、生物、化学材料,而是原物品的再生利用。比如:玻璃杯就比一次性瓶装水容器好很多,它能反复使用。“德国制造”的宗旨也是减少一次性物品,生产能反复使用的耐用品,这就是reuse的理念。


诸大建
李
您可以为我们进一步介绍循环经济理论的关键内容和最新动态吗?在循环经济的发展中我们是否存在一些认识误区?
如果说在垃圾处理问题上,垃圾分类的对立面是垃圾混合,那么在垃圾减少问题上,循环经济的对立面就是线性经济。前面已经提到,垃圾战争的高阶目标就是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变革,也就是说要用物质流闭合回路的循环经济,代替物质流从开采-制造-使用-抛弃的传统线性经济。目前,循环经济已经成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第12项目标——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的关键,就是从发展模式上避免和减少垃圾。
继第一阶段1966年生态经济学家Boulding畅想用飞船经济替代牛仔经济,我们现在已处于循环经济为主流的第四阶段。其中,英国的非赢利组织EMF对循环经济的思想整合有重要贡献。他们提出了著名的循环经济蝴蝶图,把物质流区分为生物质和非生物质,蝴蝶图的一翼是技术性循环,另一翼是生物性循环,强调在从材料开采端至埋藏回收端的全过程循环中,两头的开采和扔弃要最小化,中间的生产和使用要最大化。我自己在研究中认为,循环经济可以简单明了地分为“三进阶”,依次为废料的循环、产品的循环、服务的循环。其中,资源垃圾回收利用是最低阶的废物的循环,不涉及生产消费过程的重大变革;进一步为产品的循环,比如一次性耐用产品可以延长产品的周期;更进一步为服务的循环,不卖产品卖服务,也是现在流行的共享经济的理论基础,包括产品服务系统和各种平台经济,汽车共享如Uber、住房共享如Airbnb、中国的共享单车均是高阶循环经济的事例。
当前,我们对于循环经济主要存在四个认识误区:一是把循环经济只当作烧钱的废弃物处置而不是有挣钱潜力的绿色新经济。二是把循环经济当作废弃物回收利用的垃圾经济。循环经济最重要的是要实现整个物质流系统的闭合,包含废料、产品、服务三循环。垃圾回收只是在生产与消费外发力,再生资源利用产业只是价值链的最下游部分。三是把循环经济一味等同于3R原则。《从摇篮到摇篮:循环经济设计之探索》一书指出,我们原来在垂直方向上使用3R原则还只是生态效率,在水平方向上闭合物质流才是循环经济要求的生态效果。四是搞循环经济只发展政府主导的生态产业园区,没有发动企业搞循环经济新模式,企业才是发展循环经济的主体。一言概之,循环经济不是垃圾经济,而是要在经济中减少垃圾;不是做大增量,而是强调存量。


诸大建
李
在这场正在打响的内外兼治的垃圾战争中,对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我国而言,当前发展循环经济需要更新怎样的理念,特别是对于企业而言,应该升级怎样的行动?
全球应对垃圾挑战的总方针或垃圾革命的真正目标,是要从“来多少处理多少”的被动式垃圾处理,转变为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有意识地减少垃圾。初级的垃圾分类重在末端处理无害化,而现在的无废城市重心前移,更加强调减量化和资源化;原来单纯偏重环境治理,而今更加强调绿色转型带来的商业机会;原来侧重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而今更加强调企业的创新。
有关企业的循环经济创新,英国的埃森哲曾做过有影响的研究,认为从原材料开采、制造、流通、消费到丢弃的每个环节都有循环经济,提出了循环经济企业的五种模式——循环型材料的供应;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延长产品生命周期或再制造;共享平台;产品即服务。我国企业可以通过五种方式,从传统的线性经济型企业转换为循环经济型企业,从源头上减少垃圾,发展绿色新经济。具体而言:一是用废弃物替代原生资源充当生产的原材料。比如,很多一次性包装品都是塑料制品,而塑料的原生资源是石油。把废弃的塑料一次性包装品化解之后,其实可以作为生产牛仔裤、毛衣的原材料,这样就直接减少了对石油这种不可再生原生资源的过度开采。二是用可以反复使用、不断循环的可再生原料,包括用生物原料、可降解原料替代化石原料。比如,在汽车车身部件的材料中,可通过提升玉米、高粱成分的比例,降低对化石原料的消耗。三是成为“再制造企业”。比如,施乐复印机有一句口号,“施乐再也不制造全新复印机了”,它把旧机器所有可用部件拆解后,组装成全新的复印机,即“可再生型复印机”,这种模式也被汽车制造业所采用。四是成为产品及服务或“共享经济”企业。ofo小黄车尽管失败了,但“共享单车”这种共享经济的模式并没有失败。为什么非要拥有一件物品才能满足消费呢?何不改变一下思路——不求拥有、但求所用。通过租赁的方式,拥有了物品的使用权,生活品质也不会降低。产品的所有权仍然在企业手里,但客户是向企业去租赁服务。五是成为轻资产的p2p平台型企业。自己不制造任何东西,而是通过平台实现供给方和需求方消费者的信息沟通,进而赚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这也是今天的汽车共享平台——优步、滴滴采取的模式。所有以上五种模式,都是现阶段企业有前瞻性的绿色创新点,主旨是通过循环经济提高资源生产率,在降低物质消耗和污染排放的同时提高市场竞争力。


诸大建
李
说到互联网企业,不可不提到高速发展的电商经济带动的快递业和共享经济带动的外卖业的繁盛。据2017年的数据,以上海为例,一年的快递量达31亿件,一天的外卖量就达250万单,每单三五个包装盒的都算少。您如何看待新经济探索中衍生的新社会问题,特别是对于环境保护的某种背离?对于所谓长三角包邮区,在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落地中,循环经济和垃圾治理是否也迎来新的契机?
当前的人工智能+、互联网+、智慧+等第四次工业革命给生产与消费带来重大的新机会,同时也带来新的资源环境包括垃圾问题的挑战。电商、外卖增加导致的城市垃圾增加问题,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好在循环经济和无废经济的概念,本身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和第六次绿色创新长波的主要内容,绿色创新的思想已经渗透在新工业革命的各种探索之中。传统规模发展型意味着,若要提高产出,则需提高要素投入,即增多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而绿色创新意味着要素特别是自然资本的投入不多,但产出放大,资源生产率的概念越来越流行。事实上,在德国等欧洲国家,智能化的讨论都是与绿色化的讨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和长三角实现一体化,绿色发展是其中的关键内容。我相信,上海和长三角在以人工智能为导向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会加强智能化与绿色化的互动,捕捉垃圾治理循环经济和绿色发展带来的无限商机,成为绿色发展的领头羊。


诸大建
李
走出长三角,自中共十八大起,“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中。您如何理解这场垃圾战争与生态文明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市民素质乃至城市文明之间的关系?
讨论垃圾问题不能就垃圾谈垃圾,一定要把它放在生态文明的大体系中来认识,放在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大目标中来认识。中共十九大提出,到2035年生态文明的目标基本实现,资源环境问题得到控制。我们做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喜欢用“脱钩(decoupling)”的概念来解读这个目标,即到2035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要与资源环境消耗脱钩,其中当然包括了与垃圾泛滥的“脱钩”。以上海为例,目前上海垃圾日清运量超出2.6万吨,人均超出1.1kg,垃圾战争的阶段性目标就是要控制垃圾总量和人均垃圾的持续增长,争取不到2035年就达到峰值然后走向平稳甚至拐头向下,这也应该成为上海2035建设成为卓越全球城市的重要标志。当然,要实现这个阶段性目标,需要以市民素质的大幅提高、城市治理水平的大幅提高、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大幅提高为前提。我相信上海和中国目前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迎接我们的也许将是一个焕然一新的城市文明。


诸大建